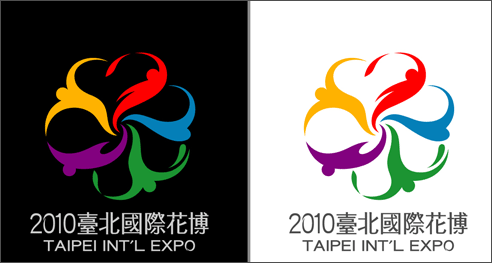(本文圖片由joe所加)
(本文圖片由joe所加)先說一下自己的感覺跟觀察。
怎麼理解台灣的歷史進程,牽涉到去怎麼理解紅姨事件。以及,左右問題在台灣,更進一步的是,西方(我主要指白人社會)的左右跟邇近國族主義興起,如先前的法國跟澳大利亞,這些年的荷蘭跟丹麥等。
老蔣及其一干麾下落跑台灣,在台灣統治,取得相當大成功。為何老蔣在中國失敗,跑到台灣會成功,這裡所謂的成功指的是「國家打造」(state making),並在台灣取得有效統治。這裡頭最大的原因即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土地上跟共產黨之間是「內戰」,但跑到台灣隔一個海峽之後是「兩國戰爭」。不論個人主觀意願否,國境戰爭讓蔣介石的藉由戰爭動員進行資源汲取、基礎行政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建構得以滲透社會,讓有效統治成為可能。
至於,在中國的戰爭狀態屬於內戰,因此,任何透由戰爭進行國家統治強化的手段,糧丁稅的汲取,並由糧丁稅的汲取過程建構社會基礎的統治機構,事實上是相較困難的。只要對人民吸血汲取過當,則在內戰形式下的人民會變成敵對陣營的支持者。哈佛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前一陣子引用了蔣家後代寧給美國不予台灣的蔣介石日記檔案寫成了一本書,《大元帥: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ai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裡頭指出蔣介石後來也似乎認為,失去中國是一件好事,如此台灣方能好好發展,否則在中國礙於內戰等諸多問題,根本無法實現有效統治。姑不論,Jay Taylor這人對老蔣相較肯定的立場,就其解讀出的蔣介石的看法,即是反應上頭所言,從內戰落跑轉進小島台灣並在美國的親暱呵護之下,透由對共產中國的戰爭狀態,在台灣進行了國家打造工程。在此不細究,日本治台末年戰時動員工業化留下的歷史遺產,對老蔣也提供了老蔣的有效台灣統治的基礎。
之後,我們都從反共復國年代下長大了。
冷戰瓦解,吹來全球化的市場自由與一體化的風潮,台灣也如火如荼地進行民主化工程。吾人方才發現,雖然在實際的國家打造過程中,台灣作為一個國家,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然而,台灣基於歷史因素,神人蔣介石時常嘴裡高喊反攻復國,作為跟美國撒嬌並取得山姆大叔的關愛眼神。陶涵去年的<大元帥>一書中也是如此認為。結果這就是實際上兩國已經形成,但意識型態跟文化上卻在反攻復國的宣稱上,讓台灣跟中國文化意識型態上的臍帶無法有效切割,儘管台灣進行了民主化工程,但這只是開放選舉的選舉萬歲總路線,而不是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意識型態上的國族想像建構,儘管李登輝後期的本土化企圖切割這條弔詭的臍帶,但摩西帶領猶太人奴隸出埃及都得在荒地上幾十年方得清洗身上的奴隸性,台灣人民根深柢固的中國性更不可能一下子就滌清。
再加上,全球化帶來的國家淡出的市場一體化風潮,伴隨台灣的民主化帶來了的是台灣的經濟自由化,並據此打破國民黨以前壟斷的部門。在內部,媒體自由化開放了,於是,喝國民黨美耐皿三聚氫氨奶水長大的媒體人(這很奇怪,媒體有高比例的外省人,我不是分族群,而是以前執此賤業時的周遭發現),大舉進入各項新興媒體,結果埋下今天李氏夫妻這種媒體人及其對台灣社會年輕一代藍丁丁的餵養。於是,中國文化臍帶大復活。
資本也開始大規模外逃。西進、南向啦….這些故事造就了台灣今天。好了,長了美耐皿結石腦袋的馬狗一干人等榮膺了島主,一下子之間,中國的鬼魂就近在眼前徘徊,且其形象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當以前用族群對抗來概括反對黨跟國民黨的對抗,本省跟外省至少還是國內格局,但是演變成「藍綠對抗」之時,就成變成了溢出一國範圍的對抗,藍的後頭有紅。
回過頭來,民萃的指控是失效的。因為,台灣不是反移民,是反中國、恐懼中國,並據此可能變成反中國人,甚至歧視中國人,例如426(死阿六仔)的稱呼。為何,因為中國人在台灣是「陸委會」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產物,其具有跟泰國、印尼等地不同。我們就沒有台泰人民關係條例、也沒有台印人民關係條例、台越….但我們就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國在台灣是特別的,執政的馬狗也是這樣做給台灣人民看。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台灣從反共變成了反中,意味著台灣將被中國給吞掉。這是國家消滅恐懼感,再加上政府政策的獨厚中國,恐懼感更加強烈了。
簡道虔指出:「『台灣有多少窮人很不好過,你為甚麼要把錢拿去補貼外國人?』歐美國家極右派炒作反移民,用的也是一模一樣的修辭。台灣現在同樣迫切的必須調整移民政策,而台灣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是中國配偶與勞工。」
問題癥結正在於此。紅姨其實講的是中國,不是普遍一律的外國(如果他們會說外國,是因為很怕大家針對中國,但其實本來就應該只針對中國)。如果今天,中國人在台灣跟外國人享有相同待遇,則的確是反移民的操作。中國到底是不是外國,他們是適用「兩岸人民關係特別條例」,而不是適用其他新移民的移民政策。舉個例子,本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要對中國特別不好,但卻被操作成對中國特別好。但,中國卻是台灣社會中最不想要好的。
如果,紅姨如果講的是「移民」問題,那都還有可能是歧視中國移民,但紅姨的所說出一般人民內心疑慮後頭的潛台詞則是,中國怎麼都跳過「移民」這一關,可以隨著中資投資進來,可以就學、考證照(雖然馬狗說不會但一定會的啦)就業,怎麼不是移民那一關卡,而是兩岸人民關係特別條例那一渠道呢?就是因為「中國」「特別」啊,正因為「特別」,也就更加深恐懼感。特別, 這個台灣膚淺民主化過程尚未處理的部分啊.
我同意要調整移民政策,因此中國人來台就學跟就業就必須比照外國人辦理,而不是特別的兩岸關係,這才會讓人放心一點。 這是因為前頭所說,台灣的蔣介石威權歷史遺留,中國這塊文化拼圖奇怪地嵌在台灣社會與人民心中。並隨著兩岸政經交融,中國有可能從文化的靈魂附身具體的政經血肉而還魂--亦即,台灣可能被統成為中國一個的特區島。
回過頭來處理政經的問題。隨著全球化帶來的市場一體化,以本國文化失落、人民失業為口號包裝著本國人民在全球化衝擊下的種種困境憂慮,於是,西方社會把問題轉嫁丟給移民。
台灣也是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市場自由化與競爭強度增加的侵襲。工作機會流失、貧富差距拉大….因為這群失根跟不利的這群人,台灣社會沒有集體代理人,因此,民萃的產生是可能的。如果我們拿阿根廷的培 龍及其 夫人艾微塔阿根廷別為我哭泣中的培龍主義當成民萃主義的理解的話,則利用「人民」這個面目不清楚的口號,取消「階級」這個基進政治意涵,則台灣社會長期的階級組織長期真空不存,則「人民」就成了只能被動員的口號。
此時(間接回應喬大),民萃的意涵有兩面,第一放在企圖用「人民」取消更具體的「階級」號召的脈絡,則民萃是右翼;第二,若放在台灣社會這種沒有階級政黨與政治的社會之下,尋求弱勢痛苦的基層「人民」動員,則相對於血緣文化的「台灣人」則是進步的。(「台灣人」放在「中國人」的對比脈絡下又是有相對進步性的,畢竟中國文化才是霸權。)左右位置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其絕對確定性的位置為何,是光譜位置上的對比產生的。這是政治動態下的實情與必然. 否則就會產生一些嘴巴左派.
上述的脈絡對比,西方社會之所以成為簡道虔的這個極右民萃反移民,有兩個條件在台灣社會是不存的。第一,他們除了米國之外,西歐都有左右階級政治,「人民」口號竄起,等於是用民萃取消本用階級劃分下的討論,若進一步將攻擊性的矛頭指向國內移民等弱勢,則並進一步成為極右的排外。第二,以荷蘭為例,剛成為聯合內閣一員的第三大民萃反伊斯蘭政黨自由黨而言,「文化」屢屢成了他們的操作口號。
回過頭檢視台灣,台灣的脈絡跟上述兩個條件不同。第一,沒有階級政治的台灣,動員弱勢「台灣人民」為口號的民萃,比起我馬鷹狗開放台灣拼經濟,不顧政治,為了拼經濟必須先圖利資本家(減稅、鬆綁種種管制—環保、勞工保護…)的菁英與自由開放為名的獨裁而言,這是進步的。第二,中國人的文化跟台灣一直沒有切割掉的中國文化尾巴太像了,因此是文化雷同而非文化差異,再加上中國在台灣的「特別」身份關係,所以簡道虔把紅姨事件當成西方那種民萃主義,事實上是有很大疑慮的。
民萃在西方也不是完全都是負面的。先前留言提到,左右界線越趨模糊之時,也是民萃趁機興起的原因之一。果若如此,西方的民萃也有可能促使左右再度疆界明確一點,當然也可能加速左右一起打擊民萃。政治是這樣動態演變的關係。
其實任何的進步宣稱,都是兩面性的。因此,的確一個從反帝反殖出發的民族主義也可能發展成壓迫弱者的種族主義,但這不過是政治演變的現實罷了。重點不是說指出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有問題,而是其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這個民族主義成了該被再度革命對抗的東西。同樣的,紅姨事件是在其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該被檢討超越的。不幸的是,台灣很多「左派」,我實在不了,其態度便是,在反帝反殖尚未成功之際,就開始把民族主義拋棄,然後卻間接地產生肯證現狀—殖民跟帝國的處境。用台灣的脈絡即是,批判台灣國族主義的壓迫性,然後一舉揚棄,因此就間接肯證了中國國族主義。對待這些事情的態度,我通常是「小心,但不壞」(dangerous, but not bad),但台灣都只有小心,而沒有不壞,所以就把嬰兒連洗澡水都倒出去了。我不是說簡道虔那文章有這樣的問題,而是說在台灣脈絡之下,我看到的是紅姨事件的進步可能跟往更好方向去的可能。
「小心,但不壞」是我一貫對待動態中政治的態度,當然這種態度是我個人自身不把自己當成外在無涉評論者,而是我是政治動態中的參與者(這不是參政表態,而是論述本身就是參政,論述位置我不是中立無涉的,我早就採取好一個策略性立場了)。簡道虔提醒了我們紅姨事件「要小心」,但我更想補充的是,「但還不壞」。

進一步就就民萃主義式的操作動員進行分析。民萃主義與動員不能把它給絕對化跟本質化,民萃大家都在用。例如,這位後馬克思主義者拉克勞(Ernesto Laclau)2007年有一本書叫做on populist reason中提到民萃主義的政治操作通常是會把「人民」跟統治者對立,然後把「人民」連結成一看看似可以有共同需求的一群人,並賦予這個需求意義。因此,在拉克勞的把民萃給拆解的步驟之下,一個以拼經濟為名的馬鷹狗,給不分人民臉孔的馬鷹狗的拼經濟並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而開啟對中國市場一面倒的開放,這即是民萃操作。
果若如此,紅姨的民萃(台灣有那麼多窮人) vs.馬狗的民萃(給全民633的拼經濟)就顯得進步了啊。因為「人民」可以被搓圓捏扁,不幸的是,沒有階級政治的台灣社會,以弱勢人民為口號,而不是以給人民633,兩者紅姨的人民內容實際多了啊。如同拉克勞所言,「人民」之所以容易被號召是因為我們都是「人民」,沒有人不是「人民」,因此新自由主義, 小而美政府....或拼經濟等空洞口號讓大家瘋狂了,但馬狗卻也犯了愚笨的錯誤,提出633跟股票兩萬點這兩個具體指標,讓一切民萃破功哩。
因此,我同意簡道虔大的某些疑慮,民萃操作動員的可怕性跟負面性,但重點不是指出這種動員手段本身的負面性,而是若要讓這種動員破攻—進一步提出,那紅姨兄提到的台灣弱勢學生問題的解決政策、助學貸款的問題、健保鎖卡的問題、稻子敗市的問題等政策。如此方能解決民萃主義動員操作乃是攀附著「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席捲人民,進一步賦予它具體的意涵內容的機會,是在台灣缺乏階級政治現實狀況下,民萃操作撞擊出的空間。
因為時間有限,先到此。總之,我歷史化跟脈絡化的方式,把紅姨事件重新理解,如此可以知道西方的民萃跟台灣的民萃意義跟脈絡的差異,並據此知道,紅姨那天的講話,其實在台灣目前社會脈絡下是進步的,而非退步的。進一步的是,那具體的政策跟落實呢。
至於,牽涉到「超克藍綠」總體大戰略,勢必以革掉藍教頭的命連帶把綠的命也給革除,然後才能進到另一個正常狀態的問題,就先不談了。
雜七雜八,實在不該寫的。只是好像大家對我昨天留言沒啥回應,我重新把故事講清楚罷了。遺漏處很多,但希望從泥沼中爬出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詳談囉!
格大根喬大的部分,我沒具體在文中指出,但文中很多也是針對兩位進行側面對話哩。
【本事件相關文章延伸閱讀】
◎國族動員與極右派——回應簡道虔〈對鄭弘儀粗口事件的一些想法〉 (by 格瓦推)(連結)
◎對鄭弘儀粗口事件的一些想法 (by 簡道虔)(連結)
◎「萬物皆備於我」新解——敬告蘇嘉全團隊,並聲援廖小貓與鄭弘儀 (by 格瓦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