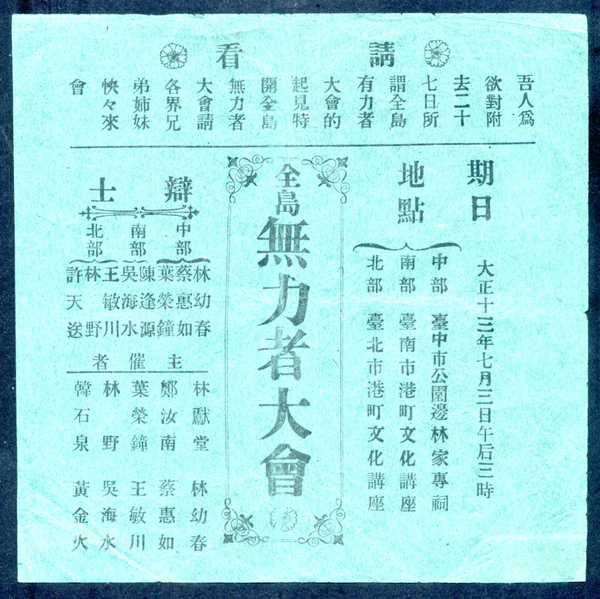有日文與漢文二版本,漢文版在後。
原作:格瓦推
日文翻譯:Makiko & 蔡亦竹
著:格瓦推
訳:Makiko & 蔡亦竹
私は尖閣諸島が日本に属する事を尊重する。それは下記の3つの理由に基づいている。
1、
1895年1月14日、日本政府は尖閣諸島の沖縄県への編入を決定し、正式に日本領とした。
つまり下関条約(1895年4月7日)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そして下関条約の際の台湾の地図には尖閣諸島は含まれていなかった。
よって台湾(中華民国)馬英九政権の「釣魚台は下関条約の際に台湾と一緒に割譲された」という主張は、事実に反する。
2、
国際法の判例では「無主地先占」と呼ばれる権原がある。
最初に無主の領土を発見し、実効統治、権限の行使を行ったものがその領土の主権者となる根拠のひとつとして認められる。
日本政府は1896年以来(本年から日本政府によって魚釣島が国民に借地される事実に基いて)、絶え間なく実効統治を続けている。それに比べて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は文献記録以外、一切の管理事実は皆無である。
3、
1951年のサンフランシスコ条約により、第二次大戦後、日本は台湾を放棄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南シナ海の澎湖島・南沙諸島の一切の権利を放棄したが、尖閣諸島に関しては述べられていなかった。
尖閣諸島は沖縄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の管理下に置か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1971年日本とアメリカは沖縄返還協定に調印。それによりアメリカは戦後以来管理して来たこれらの諸島を日本に返還した。
尖閣諸島は沖縄の一部分となり、当然これは日本の領土となった。
歴史上での先占、実効統治、最も重要な太平洋戦争の条約等に基づき、日本が合法かつ合理的に尖閣諸島の主権を有するという事実には疑う余地がない。
台湾の中華民国政府は百年来、何の統治行為も行っておらず、終戦後台湾の管理を受け継いだ際にも、尖閣諸島の主権を主張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1969年に尖閣諸島周辺の海底に石油、ガスなどの資源が埋蔵されている可能性が指摘され、
1971年 初めて台湾の蒋介石政権(終戦後、台湾の管理を任された中国の将軍で、台湾を統治した大統領)がこれは中国の領土であると主張しだした。そして地図を改ざんした。
恨みのこもった過激な発言というものは注意を引きやすい。最近の台湾の尖閣諸島に対しての反対運動が引き起こした反日言論に対して、
私はいち台湾人として、台湾と友好だった日本社会に誤解されないために台湾人民の民意をここでしっかりと説明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中国から来た入植者、中国国民党の支配下で、今の台湾の国民党政府は反日教育を押し進めている。台湾国民の教育は、大中国史観の妄言に満たされている。
台湾人のほとんどは親日派なのだが、国民政府は歴史教育で(日清戦争、太平洋戦争、日本の台湾統治)反日感情を植え付けようとしている。
今の尖閣諸島問題に関しては台湾(中華民国)の親中派の勢力が中華人民共和国と共謀しており、台湾人に中国民族主義を煽ってやまない。
例えば海上で挑発行為をしたり、国会で様々な演出したり、街頭でのデモ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の洗脳ーこれは全て親中派が勢力を総動員してやったことである。
声大に叫んで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けれども、実際の台湾を代表する声ではない。
尖閣諸島の主権と漁権は別にすべきだ。
戦後の歴史上、台湾人の李登輝総統(初めての台湾人の大統領)と陳水扁総統(台湾人の大統領)
二人の台湾人の大統領は尖閣諸島における日本の主権を尊重し、台湾の漁民の生活を守るため、
漁権の保護のために働き、李登輝総統は15回、陳水扁総統は7回も日本と台湾の双方がうまくいくように交渉した。
中華人民共和国寄りで反日感情がある今の馬英九総統は、主権と漁権を一緒にして主張し始めた。
漁民の生活を犠牲にしても勝手に自分の個人的な意向を優先した。
台湾での尖閣諸島に対する反対運動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と中華民国が合作して演出したものであり、台湾人がやったことではない。
彼らの本当の目的はこの島を取ることではない。
中華人民共和国にとっては、この反日運動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国内の権力闘争から注目を逸らすための手段にすぎない。
そして中華民国(台湾)から見れば、これは中国大陸と台湾が共同で反日尖閣運動を煽って、両岸の合併を促進するためである。
中華人民共和国と馬英九政権の双方が主張する、「尖閣諸島が中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り、台湾もまた中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る」という言い方は、
これは民族主義による史実の改竄であり、嘘である。
なぜ台湾の社会で、ある程度の反日の声がでるのか。その原因は歴史に対しての無知から来るもので、親中派勢力の工作によるものだ。
願わくば日本の社会においては、このようなごく少数の過激な言論を台湾の民意だと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
台湾人民が中国国粋主義に染まっていると思わないでほしい。
台湾はひとつの国家として、歴史的にも文化的にも日本と深い絆で結ばれている。
台湾の民間人は日本に対して本当に親しみをもっており、友好的な想いはずっと続いている。
いまは政治権力を総動員して世論を操作しているけれど、将来この勢力が衰退すれば、再び真実が明らかになる事でしょう。
【漢文版】
基於三個原因(連結),我充分尊重尖閣諸島屬於日本的事實:
(一)
日本於1895年1月14日正式將尖閣諸島納入領土,歸沖繩縣管轄,無涉於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且馬關條約所黏附的台灣地圖,不包括尖閣諸島,馬英九政府所主張「釣魚台是依馬關條約隨台灣割讓給日本」並非事實。
(二)
依國際法庭案例:「發現僅能構成取得領土的初步權力,若領土主權發生紛爭,則需進一步證明該國發現後有行使主權之行為。」日本政府於1896年起(有日本政府租借予日本國民移墾的事實)不間斷對尖閣諸島的實效統治迄今;相較之下,中國除了以文獻紀錄提及該地,一切管理事實皆付之闕如。
(三)
根據舊金山合約,戰後日本需放棄台灣、澎湖與南沙群島一切權利,並無提及尖閣諸島。該地乃隨沖繩託管於美國。1971年美日簽署「沖繩歸還協定」,歸還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交給美國託管的島嶼。尖閣諸島作為沖繩的一部分,當然也成為日本的領土。
就歷史上的先佔、實效統治等因素,以及最關鍵的太平洋戰爭相關條約,日本乃合理合法擁有尖閣諸島主權,殆無疑義。百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從未在尖閣諸島進行任何統治行為,在戰後接管台灣之際,也未曾宣稱擁有尖閣諸島主權。直到1969年尖閣諸島周邊海底被探勘出可能埋藏石油與天然氣,1971年蔣介石才開始主張該地是中國固有領土,並竄改地圖。
激進的仇恨言論較容易受到關注。對於台灣近日因保釣運動而興起的少數仇日言論,身為一個台灣人,為避免一向與台親善的日本社會誤判台灣民意,必須做一些說明。
在來自中國的殖民者——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的歷史教育充滿大中國史觀的謊言。儘管台灣人普遍親日,但在觸及某些歷史議題時(如日清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治台),非常容易被國民黨挑動仇日情緒。
在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一事,台灣的親中勢力與中國聯手,煽動一種仇日的中國民族主義。不論海上的挑釁行為、國會殿堂的作秀、街頭的示威、網路上的叫囂,多數來自於親中勢力的動員。聲音雖然亢奮,卻不能代表台灣。
主權與漁權可脫鉤。基於歷史事實與戰後條約,台灣的李登輝總統與陳水扁總統在兼顧尊重日本主權與照顧台灣漁民生計的考量下,分別與日本進行15次與7次的尖閣諸島周遭的漁權談判。現任總統馬英九卻基於個人的中國認同與仇日情緒,將漁權綁架於主權問題,意圖犧牲漁民的生計,偷渡個人的意識型態。
以往台灣的保釣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染指日本領土;這一波保釣運動,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政府聯手演出,但真實目的都不是尖閣諸島。對中國政府而言,仇日情緒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對馬英九政府而言,塑造「兩岸華人共同保釣」的氣氛,以作為兩岸合併的催化劑。中國與馬英九政府宣稱尖閣諸島為中國固有領土,與其宣稱台灣為中國固有領土,風格如出一轍——都是昧於史實的民族主義謊言。
台灣社會的仇日聲音只是少數,其原因除了對歷史無知外,還有親中勢力的動員。希望日本社會莫因少數激進的仇日言論而誤判台灣民意,勿以為台灣的國族認同已傾向中國。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主體,在歷史與文化上,與日本有深厚的羈絆。佔台灣社會多數的對日友善聲音,目前被大量動員的仇日浪潮所淹沒,但不代表消失。衷心期待日本社會不要被中國與台灣政府聯手動員的假議題所蒙蔽,台灣民間對日本的親切與友善,一直真實地存在,也將在政治動員的力量消退後,再次清楚呈現。
【延伸閱讀】
〈為什麼釣魚台是日本的〉(連結)